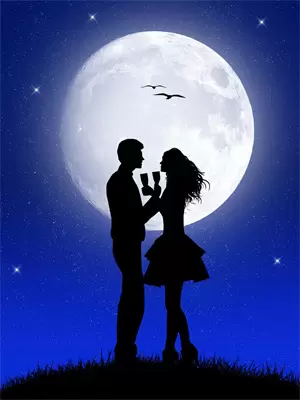---第一章:熟悉的仪式老陈又一次站到了民政局门口。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,
卷起几片早凋的梧桐叶,在他脚边打着旋。眼前的台阶灰扑扑的,
缝隙里钻出几丛顽强的青苔,和他记忆里的样子分毫不差。
他下意识地紧了紧身上那件穿了多年的棕色夹克——还是柳絮很多年前买的,说耐脏,
适合他这双总也洗不干净油污的手。他低头,摊开手掌,那双手指节粗大,
指甲缝里还隐隐透着洗不净的黑色油渍,像岁月烙下的印记。他用拇指的指腹,
反复摩挲着食指侧面的老茧,然后,抬起手,习惯性地摸了摸夹克内衬左边那个口袋。
手指在内衬口袋的位置摩挲了一下——那里鼓鼓囊囊的,
装着六本边角已磨损的暗红色小册子。那是他们过去六年,在同一天,
从这个大门里带走的“战利品”。而今天,他们将在这里,拿到第七本。他转过头,
看向身侧半步之外的柳絮。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羊绒衫,
颈间系着一条他很多年前出差时给她买的丝巾,颜色已经不那么鲜亮了,
但她依旧仔细地熨烫过,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。六十三岁的人了,头发染得乌黑,
梳得一丝不苟,只是眼角的皱纹,像被时光精心雕刻过,深一道浅一道,
记录着他们共同走过的四十多个春秋。她平静地看着前方排队的人群,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,
仿佛只是在等待一场寻常的电影开场。老陈心里叹了口气。这场景,太熟悉了。
熟悉得让他心头泛起一种近乎麻木的钝痛。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。
前面是一对挽着手、低声说笑的小年轻,女孩头上别着白色的头纱,男孩西装笔挺,
一看就是来领那份红彤彤的喜悦的。另一对则隔得老远,各自捧着手机,
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厌烦与冷漠,标准的“离婚相”。老陈和柳絮排在后面,
两人之间保持着半个人的距离,一种无形的、名为“默契”的沉默横亘在他们中间。
第二章:裂痕的起点——第一本离婚证记忆像被撬开了一条缝,六年前的今天,
清晰地浮现出来。那也是个秋天,为了阳台上那盆茉莉花。那是柳絮的心头好,一株老桩,
花开时满室清香。她精心侍弄了十几年,用的是一只她陪嫁带来的青花瓷盆,釉色温润,
画着缠枝莲,她说有她老家的味道。那天,老陈给花浇水,手里拿着厂里带回来的图纸,
心里琢磨着一个技术难题,一走神,手一滑——“哐当”一声,瓷盆碎了,
泥土、瓦片和茉莉花的根须散落一地。柳絮闻声从厨房冲出来,看到一地狼藉,
脸色瞬间就白了。“陈建国!你……你知不知道这盆……”老陈正为图纸上的难题心烦,
见她这架势,火气也“噌”地冒了上来:“不就一破花盆吗!碎了再买一个就是了!
嚷嚷什么?”“破花盆?你说得轻巧!这是能买得来的吗?”柳絮的声音带着哭腔,
“我跟你说了多少遍,浇水的时候当心点,当心点!你心里除了你那些图纸,还有这个家吗?
”“我没这个家?我没这个家我天天加班加点是为了谁?供房、养家、儿子上学,
哪一样不是钱?一盆花而已,至于吗你!”“至于!当然至于!在你眼里什么都至于,
就我的东西,我的感受不至于!”争吵像野火燎原,烧掉了最后一点理智。
乱扔的袜子、她唠叨的饭菜、他永远缺席的家庭聚会、她无法理解的工作压力——在这一刻,
借着破碎的花盆,轰然爆发。“这日子过不下去了!离婚!”柳絮红着眼眶,
嘶哑地喊出这句话。老陈梗着脖子,额头青筋暴起:“离就离!谁不离谁是孙子!”第二天,
他们真来了。就是在这个民政局,排的就是这个队。当时的工作人员是个脸圆圆的小姑娘,
看看他们,又看看结婚证上登记的三十多年婚龄,欲言又止,
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劝了句:“叔叔阿姨,都快金婚了,
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……”两人都铁青着脸,一言不发。手续办得很快。钢印戳下去,
“哐”一声轻响,老陈觉得那印记像是烙在了自己心上。
拿到那本崭新的、暗红色的离婚证时,两人都愣住了。那小小的本子,拿在手里竟有些烫手。
走出大门,外面的阳光晃得人眼晕。老陈看着柳絮单薄的背影微微佝偻着,
想起她年轻时就怕冷,秋天总要他捂着的手,下意识地想脱下外套,手伸到一半,
才惊觉自己已经没了这个资格。那晚,他回到那个忽然变得无比空旷和冰冷的家。
沙发上没有她织了一半的毛衣,厨房里没有她温着的、总是嫌太咸的汤,
空气里也没有了那株茉莉的清香。他坐在客厅的椅子上,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,坐了一夜。
第二天傍晚,他鬼使神差地走到他们以前常散步的公园湖边,
果然看见柳絮一个人坐在那张掉了漆的长椅上,望着被秋风吹皱的湖面发呆,背影萧索。
他走过去,干咳了一声。柳絮抬起头,眼睛肿得像核桃。“你……吃了吗?”他哑着嗓子问。
“没。”“……回家吧,”他沉默了片刻,说,“外面风大。我……我去下碗面条。
”柳絮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站起身,跟在他身后,隔着两三步的距离,像个小影子,
一步步挪回了那个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家。没有手续,没有誓言,只是一个人回了头,
另一个人开了门。那本崭新的离婚证,被老陈塞进了夹克内衬口袋的最深处,再没拿出来过。
第三章:循环的建立与演变此后,每年的同一天,仿佛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,
他们都会准时出现在这个民政局门口,排队,办理离婚。这成了一个荒诞又郑重的仪式,
一个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、清理情绪垃圾的出口。第二年,原因是他乱扔袜子,
她说他看着就烦。工作人员换了个年纪大些的大姐,看到他们去年的记录,眼神古怪,
但没多问。签字时,老陈的手有点抖。出来时,天下起了小雨,他们共撑着一把伞走回去,
胳膊偶尔碰到一起,又迅速分开。第三年,是为她炒菜咸了,他说没法下口。柳絮在签字时,
笔尖顿了顿,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。那天没下雨,但风很大,吹乱了柳絮的头发,
老陈下意识地想帮她拢一下,手抬到一半,又放下了。第四年,
好像是为了一句无关紧要的拌嘴,甚至不需要具体的理由,只是觉得到了这天,就该来了。
他们赶上了瓢泼大雨,共撑着一把伞,半边身子都淋湿了,狼狈不堪。回去后,
老陈罕见地打了几个喷嚏,柳絮默默地熬了一锅姜汤,放在他面前。第五年,排队时,
前面那对闹离婚的小年轻吵得不可开交,差点动起手来。
老陈莫名其妙地吼了那男的一句:“吵什么吵!有什么好吵的!能过过,不能过好好散!
”吼完,他自己都愣住了。柳絮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那年,他们办完出来,
在街角那个流动摊贩那里,买了一份烤红薯,热乎乎的,一人一半,分着吃了。很甜。
第六年,也就是去年。他们更加沉默,流程熟悉得像在走过场。拿到离婚证的时候,
老陈看着柳絮眼角深刻的皱纹,心里猛地一抽。他突然发现,他们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,
都在不可逆转地老去。那六本暗红色的离婚证,像六块冰冷的墓碑,矗立在他们婚姻的路上,
标记着一次又一次的“死亡”与“重生”。它们证明不了对错,
只证明了他们拥有一种古怪的、近乎偏执的韧性。
第四章:婚姻的走马灯在排队等待的这一个多小时里,老陈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,
闪过了他们的一生。他想起第一次见柳絮,是在纺织厂的联谊会上。她扎着两个粗辫子,
穿着碎花衬衫,正在唱《茉莉花》,声音清亮亮的,像山泉水。